
艺术的力量或泰莱夫的长矛 / Bertrand Leclair,MF 版 / 215 页,18 欧元。
作家的原材料不是思想、主题或伟大的故事,而是语言。自从他的第一本书《安慰的工业》(Verticales,1998)以来,伯特兰·勒克莱尔继续传播这种使其焕发活力的气息,动摇了公认的表述中死气沉沉的语言。他现在出版了一本交替小说和文学散文的书,衡量文学作为艺术(而不是作为文化消费的对象)的含义。在我们不断听到文学中的阶级叛逃者的时代,写一部“社会小说”就足够了,《艺术的力量》和《泰莱夫之枪》更令人不安,但也是一个来源喜悦。与它的作者会面。
您的书是您在一次研讨会上进行的反思的产物,该研讨会将文学视为“一种艺术实践”。您是如何从本次研讨会开始接触到这本书的?
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有机会主持一次非正式研讨会,其目的是质疑写作和阅读的实践,不是为了教授任何东西,而是为了将我所学到的文学实践作为经验来传播。然而,与其说是反思,我更愿意谈论一个想法:这种希望始终保持活力的想法是本次研讨会的根源,因为它在交流中受到欢迎,可以部署吗?摸索。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基于您对两个经常混淆的概念(知识和知识)所做的区分,在您看来,第二个概念比第一个概念更有成效。为了什么 ?
我并不优先考虑知识和知识,它们显然是有联系的,但努力表明它们也可能是矛盾的。知识具有社会必然性,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其追求是艺术姿态的基础——知识和知识因此形成了一种二分法,我将其与其他二分法联系起来以澄清它,其中一个可以在这里使用,例如:权力和权力可能。权力在强加自己的那一刻总是源自一种形式的权力,但很快,它知道自己的权力注定会衰落,因此寻求巩固自己,以便引导其他权力来源为其服务。
知识之于知识,正如权力之于权力。
知识之于知识,正如权力之于权力。没有人能够囤积知识,除非他们将知识冻结成知识。所有已建立的知识都有一种机械倾向,对可能“瓦解”其学术秩序的知识冲动保持警惕。那么,硬化症正在等待着他和我们。相反,艺术永远不会停止冒险到集体无知的边缘,这是艺术家的游乐场,这就是它成为获取特定形式知识的途径。
在世界的永恒存在中,没有什么可以停止,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些知识被冻结或囤积:它是流动的,在我们的言语之间流动,就像水在手指之间流动,而且来自干渴。因此,形式在艺术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对于知识来说就像瓶子对于水一样——只不过它总是需要被重新发明,内容和容器是密不可分的。
在本书中,您再次广泛回顾了普鲁斯特和《追寻逝去的时光》,而您之前的文章《普鲁斯特的火车》(2) 则完全致力于此。他的什么特质特别能阐明你的观点?
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品之一,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虽然它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但《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千层酥,普鲁斯特认为它“更诚实、更精致”,而不是标题为“追寻真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本启蒙书。
关于同一主题: “普鲁斯特的火车”:鲜为人知的目的地与尼采和兰波的作品同时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场再现秩序的革命,以重塑精神生活:正如他重复的那样,通过在艺术姿态中突出“本能”而不是智力,仅靠智力,然而,能够授予“本能属于它的至高无上的王冠”,他证明,在塑造我们生活方式的宗教废墟中,提升到真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挖掘在由理性和习惯所固定的共同表征的框架下下降到那里,他说:沿着我们的存在展开的时间顺序垂直下降到那里,这个水平时间本身只是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表征,因为它对我们的社会功能至关重要。 。
在我们的精神沙漠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源头作品。
研究准确地证明了艺术的力量能够揭示“真实生活”,即使只是在瞬间,“真实生活”只不过是对最物质生活的公平感知,一旦摆脱了普通的表征,就可以轻松地被刻板印象:转瞬即逝的真理,心理理性难以捉摸,但永远活跃。正是在这一点上,《追忆似水年华》开辟了一条通往快乐的新道路,一种快乐,普鲁斯特写道,它必须被真正理解,“就像一种确定性,足以使死亡对我来说变得无关紧要”。在我们的精神沙漠中,有时,当我们失去意识时,被焦虑淹没的世界似乎也处于失去意识的边缘,《寻找》是一部源头作品。
您对“我们的社会缺乏精神维度”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感到遗憾,但并未哀悼宗教的崩溃。 (我们)对什么关闭?
轻描淡写地说,我对西方宗教的崩溃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如果我对我们缺乏利用本应由此产生的知识自由的渴望感到遗憾的话,一旦划定宗教领域的禁令被废除,我就不会感到遗憾。解除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罗杰·凯略瓦(Roger Caillois)提出的宗教定义更好的了,当时他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非常接近,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痛苦中写下了《人与神圣》(L'Homme et le Sacré)(1939):宗教是神圣的管理,无论是在任何意义上,无论是管理有机体还是仔细测量的药剂。
关于同一主题:伯特兰·勒克莱尔:“我从内部触及我的性格”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启蒙运动的无限欢乐时刻,对应着宗教“无知庇护所”的崩溃,然而,它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使我们摆脱它声称日复一日管理的东西:对未来的无知,以及一切与起源和终结或终结之谜有关的事物,无论是每个人的还是宇宙的。
您在第一页中写道,“这篇小论文的利害关系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呢?
这里的副词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还有什么比在表征系统的核心发挥思想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吗?因为它编织了我们共同的现实,这种表征系统同时使我们能够理解世界,并将人类这种会说话的动物与人类隔离开来。现实?将文学简化为娱乐,无视无知以建立知识并尽快建立权力,这些无论有意无意,都是政治纲领。不屈服同样是政治性的,尽管我们离萨特式的承诺还很远,而萨特式的承诺在合作结束时是必要的。
词源学邀请我们去发现,语言的奥秘在多大程度上比我们对那些声称将语言变成我们自己的人了解得更多。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文学就是风”,这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笑话:我们阅读、写作时所经历的风,有时是无法决定的,它传播花粉,驱散灰烬,这风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每一页活生生的书页中,无法简化为知识或技术,为共同语言注入生命。风令人不安,但它对生命至关重要,如果它很少有助于形成一种众所周知的秩序,那么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空气。
关于同一主题:伯特兰·勒克莱尔(Bertrand Leclair)的“在阳光的范围内”:旅行之王您经常诉诸词源,从您的第一本书开始就一直这样做。这是一种在单词被固定使用之前(如果不是过度使用的话)回到单词含义的方法吗?
因此,词源学邀请我们深入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表征的来源,并发现语言的神秘性在多大程度上比我们对那些声称自己拥有语言的人了解得更多。我不知道有什么关于智慧的专着比非常非凡的罗伯特的《法语史》更令人愉悦、清晰的了。我们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就像在能指浓密的森林里寻找光线照耀的空地一样——因此,在一千个例子中,拉丁动词legere产生的家族,当然,它给出了“阅读”,但也其中包括“pick”(读起来是用眼睛挑选)、“elect”、“neglect”及其反义词“intelliger”,这是法语中存在但非常缺乏的动词。
关于同一主题:伯特兰·勒克莱尔:分离焦虑你经常通过用其他词语、其他图像重新表述来重复刚刚所说的话。然后你写:“换句话说……”这仅用于教育目的吗?
当我们想要传达的内容总是有多个方面时,与其说它是一种强调要点的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支持、阐明不同观点的表述方式。也许对某种形式的教育立体主义有可疑的倾向……
你回顾一下你的写作历程。关于你的开始,你有这样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话: “简而言之,写作首先是剥离自己,即使这意味着撕碎它们,也剥离掉别人从小通过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判断而贴在我们身上的句子和想法。 ,他们不知不觉地或无意地强加的思维模式,极大地强化了禁令,使每个人都有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更加令人内疚,因为它没有意识到它是非常普遍的。 »今天,您认为写作对您来说是一条成功的解放之路吗?
那就太自命不凡了!一切都必须重做,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知识,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大海中的瓶子里见证知识,那就是作品。我想说的是颠倒你的问题来提出一个必然性:我很难理解那些似乎除了娱乐之外与艺术没有其他关系的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简而言之,我无法想象思想如何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生存;光是想想就让我窒息。
简而言之,我无法想象思想如何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生存;光是想想就让我窒息。
你正在写一本基于理性的反思之书——你甚至谈到了“权威之词”——同时你谴责了对知识的垄断。如何走出这个悖论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的批判倾向,也就是说政治性的:渴望在社会宇宙中存在我们生活的艺术维度,而这个宇宙想要忽视……我多次提到这个悖论。也就是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分享知识领域的旅程;被称为知识或权威地位将是失败的——除非我们恢复“作者”一词的词源深度:作者然后成为“保证人”,无非就是语言生命的保证人,这种语言既是我的,也是每个人的,它给我们带来了限制,也让我们感到惊讶。
每周在家中都会收到 Polit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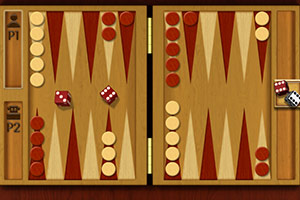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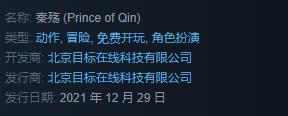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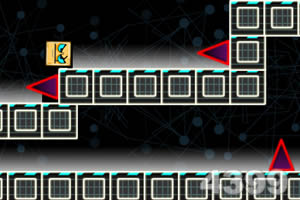


留言